铭心刻骨“疙瘩楼”
作者 | 王鹏飞
“难忘疙瘩楼,儿时爬墙头。铭心又刻骨,快乐且无忧”,这是我自拟的打油诗。
每每走过“五大道”河北路上的“疙瘩楼”,禁不住地心潮激荡,唤起我儿时居住在“疙瘩楼”生活往事的许多美好回忆。

这是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样的文化,给予我们这一代人心灵之中挥之不去的烙印。

纪录片《五大道》讲述“疙瘩楼”时,提到疙瘩楼建于1937年,设计者为意大利建筑设计家保罗·鲍乃弟。
该建筑为三层半砖木结构八门联体洋楼,其中,一层在半地下,二层为圆拱形正门所在,由高台阶通达,三层为阳台,四层为一排百叶窗,百叶窗上部设有绿色的遮阳棚。
疙瘩楼是毗连式里弄住宅,该住宅类型受到西方联排式住宅建筑形式的影响,整体由单元联成并组合,布置较为紧凑,房间朝向和采光通风条件良好。
建筑外立面为清水墙面,上面铺有琉璃砖并镶嵌着一些的疙瘩砖,构成建筑主体的粗糙质感外观,圆形的门楣之上设有圆拱半凹悬挑的曲尺形阳台并设有珍珠串式栏杆、窗边设有水纹花饰。
疙瘩楼是一座具有浓郁的意大利风格的西洋公寓式建筑,每个院,有院墙分隔。

据有关资料介绍,位于当时的天津英租界的威灵顿道和香港道交口转角处(今和平区河北路与睦南道交口转角处,今河北路285—293号)的疙瘩楼最早曾是英国先农房地产公司的公寓。
疙瘩楼曾为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在天津的故居,其中河北路291号疙瘩楼二楼,曾租给名医陈鸿谋开的诊所。现今疙瘩楼二楼马连良曾经的书房还保留着马先生的老照片、蟒袍、烟杆等物品。
据溥仪的堂弟、爱新觉罗·溥佐先生回忆,当年的“疙瘩楼”曾“车如流水马如龙”,经常出入于此的宾客有靳云鹏、鲍贵卿、曹汝霖等政要以及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等京剧艺术大师。

作者曾经的家。
我家居住的“疙瘩楼”,位于马场道与睦南道之间的河北路(原为河北南路)287号(新号291),是在上世纪“大跃进”那年在此落户而居的。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们家是作为随军家属落户到天津的第一个家。我是1956年出生的,差不多整个童年时期都是在“疙瘩楼”度过的,经历了学龄前、上小学、文革等等。
我记得,我家住的疙瘩楼287号院,旁边隔一个院过去是“合作社”,买副食品、买菜等都在这里。
从“合作社”过去是粮店(那边就是新疙瘩楼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住在疙瘩楼每幢楼院的区政府领导、区政府干部居多。
我家是邻街二层楼朝西的一间大房子有40多平方米,一进门就能看到靠墙边的一个很讲究的欧式壁炉,可我从小到大没看到家大人使用过它,它只是我们家中的一件摆设。
我们家没有用过壁炉做饭,做饭是在过道点一个煤球炉子,点煤球炉子时,满楼道都是烟熏火燎的。

上图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夏天,当年在位于和平区河北南路一住户阳台上,一名80后出生的儿童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块饼干,一边唱着歌谣……童真快乐溢于言表。
照片上,该儿童身后还在使用的煤球炉子等,是当时生活现状的真实写照。
在我家住的疙瘩楼院内有一棵硕大高耸的槐树,那树梢高过了疙瘩楼的四层楼楼顶,哎,别看疙瘩楼只有四层楼高,可它相当于现在的单元楼的六、七层楼高,所以住在疙瘩楼的房子里感觉特别宽敞。
当槐树开花时,我们这些顽皮的男孩子就爬上院内的疙瘩墙头用竹竿打下一片片的槐花,然后再把落地的槐花收集起来拿回家,家大人将槐花洗净掺合上棒子面放在蒸锅里蒸熟,老远老远的都能闻到那槐花的喷香,吃起来又肉头又香甜。
当然,我们也曾自己丰衣足食,在疙瘩楼一楼的后院的一块狭长的土地上,栽种过玉米、丝瓜、扁豆角和养小鸡、养小鸭等,还真获得过不小的收获。
爬墙头,粘蜻蜓,是我们疙瘩楼小孩子喜欢玩的。夏天时,高耸的大树树枝上落有各样的蜻蜓,我们管小一些的单一色的蜻蜓叫“老褐”、“黑老婆”,个头大一些的身子尾巴上有金黄色圈圈儿的叫“花里虎”,尾巴头带两个小圈圈的叫“花里豹”,全身呈翠绿色的叫“大老青”,还一种中不溜大的蜻蜓叫“小鬼儿”特狡猾,一会儿落一会飞,好似故意逗你玩。
这其中“老褐”是最傻的,最容易被粘到或捉住。小孩子们用铁罐头盒熬松香,熬松香时里面需放一点油,这样就熬成的粘子不会凝固,然后用小木棍把粘子抹在细细长长的苇竿尖头上,苇竿的高度粘不到蜻蜓时,就爬到墙头上(要说这也是很危险的)举着苇竿去粘,只要粘子触到了蜻蜓的翅膀,全凭蜻蜓怎样挣脱都逃脱不掉的。
小孩子粘下一个蜻蜓来,先把蜻蜓翅膀上的粘子抹一下让翅膀展开,再把蜻蜓的脑袋夹在手指缝中间,这样蜻蜓跑不掉也不会死,又不影响举竿再粘下一个蜻蜓,直到两只手指缝间夹满了蜻蜓,这才算凯旋而归。
也有时候,小孩子们爱跑到马路上去扑捉蜻蜓。那是在“喷水车”刚刚喷水过后,泊油路湿漉漉的,“老褐”飞的很低,有时也有“黑老婆”什么的,小孩子们就脱下衣服追着蜻蜓扑打,蜻蜓被扑落到地上就“晕了”,捉到手里后等到它醒来,小孩子们就在蜻蜓的尾巴上系根长线,一手揪着线头放蜻蜓飞,自己在后面跟着跑,开心的不得了。
有时,小孩子们光顾跑着玩了,没注意“喷水车”从身后开过来了,一下子被喷了一身的水。不过,小孩子们也经常跟“喷水车”淘气,在“喷水车”迎面开过来时,小孩子们一群一群的跑到“喷水车”车后两边,一边跟着“喷水车”跑,一边在“喷水车”的喷嘴口那里玩水,弄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除了爬院墙,我们疙瘩楼小孩子爬墙头的领域逐渐扩大,胆子也越发大了。在我家住的疙瘩楼一楼的后院,我们小孩子爬墙头从底层爬上相当于三层楼高的阳台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有了爬墙头的“本领”,于是眼界大开,我们经常从疙瘩楼这个院爬墙头到那个院,还通过四楼的阳台爬上疙瘩楼的屋顶,踩着锥顶瓦砾由南走到北然后在折回来,更玩悬的是,我们还竟然溜着斜屋顶到屋檐最边上从上往下望高,真得说那砖头瓦砾结实,不然我们这些小孩子兴许早就一命呜呼了。
爬墙头也使我们疙瘩楼的小孩子们很容易串连在一起玩儿,那时候经常能听到院子里传出来的欢快的童声儿歌。
记得经常一起玩的一种游戏,我们分成两拨的小孩儿,也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一边排成一行,大一些的男孩子或女孩子站在中间,一个拉着一个的手,一边往前走一边唱:“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
接着,对面的一排孩子也手拉手的一边走一边唱:“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然后就是“被要求的小孩子”站出来比试“本领”,直到一个对一个的比试一方将另一方取胜。
除此,我们还经常玩什么拍毛片啦,弹球啦,捉蛐蛐啦,抽冰猴啦,藏蒙个啦,跳房子啦,踢罐电报啦、放风筝啦等等,
小时候在疙瘩楼,我记得小孩子们常聚在一起在路边上唱天津快板似的顺口溜,如“来到了天津卫”、“拾毛篮子背大筐”等等。
后来根据这个儿时记忆,我创作了一个天津快板小段“来到了天津卫”,该文如下:
来到了天津卫
我来到天津卫,是嘛也没学会。
学会了开汽车,手生还打哆嗦。
一个没留神呀,违规就闯了祸。
要藏没处藏呀,想躲还没处躲。
怎么那么快呀,警察就找上我。
扣分又罚款呀,我真是没了辄。
工作还没着落,兜儿里钱不多。
罚款交不上呀,我急得拍脑壳。
我是真倒霉呀,我是真的窝火。
这还不算完呐,回家得挨数落。
我劝大家伙呀,千万是别学我。
再来天津卫呀,可不能这么着。

人世沧桑,岁月如梭。现今的“疙瘩楼”,虽则老楼依旧,已被现代化的时代氛围所笼罩,临街的底房几乎都成了商家的门脸,灯红酒绿,车水马龙……
那时的孩童亦已迈入老者,然而,童心未萌,往事如烟,疙瘩楼刻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如陈酿的美酒味甘绵长滋润心田。
当年“五大道”上的小同学

前排右一为王鹏飞、左一为安崇伟、第二排右一为刘爱奇、中间为孙玉玲、第二排左一为马文民。
上图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年在天津市和平区西安道第二小学上学的这五名同学,在居住在和平区马场道居民楼(现为天津市住宅集团办公楼)的同学马文民的家里,上学习小组时拍摄下的照片。
照片现今,他们都已成为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当年的西安道第二小学没有了,原校址现今已是西安道消防救援站了。


我的中学是反修中学(后改为和平中学),原址现为实验小学。

上图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年我们在位于和平区河北南路上新华职业大学(重庆道、大理道之间的河北南路路段)上学的79级汉语言文学某班的部分男同学和授课老师的合影。

上图为79级某班的部同学和授课老师在市民革(重庆道与河北南路交口)会议室开座谈会时的合影。
新华职业大学原为新华业余大学,79级是在国内刚刚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上此学校的同学。
很多走上党政、公安、教育、文学杂志编辑、新闻记者等工作和领导岗位上的同学,都是取得的了这个学历之后开始的职场旅途。
王鹏飞简介:
王鹏飞,男,天津消防总队主任记者(退休),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公安局授予警营艺术家,知名画家,多年来,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社会报》、《天津日报》、《今晚报》、《中老年时报》、《中国消防》杂志等报刊媒体发表许多新闻稿件、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摄影、书画作品等,著有文学作品集《一个窃贼的二十四小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集《火灾与你有多远》(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以上为作者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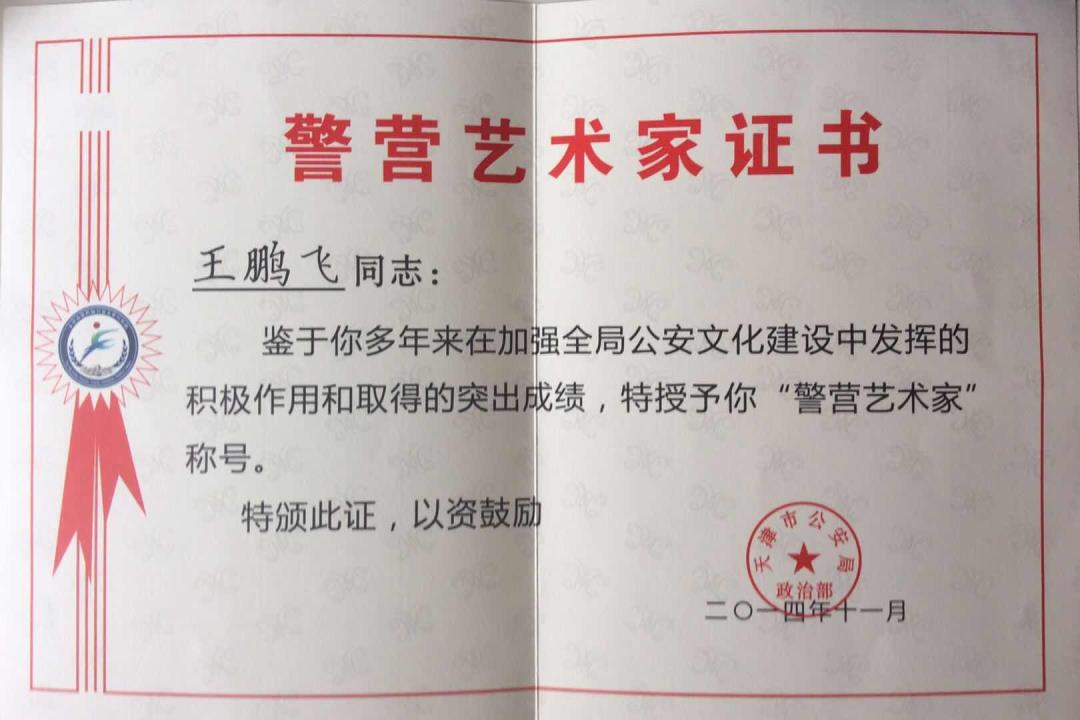
天津市公安局授予作者的警营艺术家证书。
完
作者王鹏飞,河北省海兴县人,1956年2月生人,1958年随军家属落户河北路,后搬至大理道、重庆道居住;天津作协会员。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关于我们
“情系五大道”公众号、头条号汇集了五大道人讲述的老故事及五大道人的文学、摄影作品等,旨在重温五大道老时光、探寻五大道人的生命轨迹、弘扬五大道的人文精神。欢迎新老五大道人踊跃投稿,文字、口述均可(有意者请在私信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本号刊登的文章(不代表本号立场)均为原创,不经许可请勿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